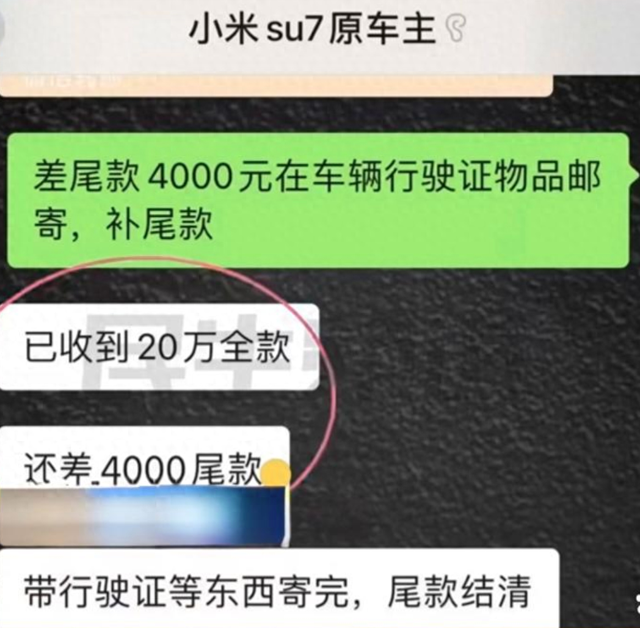4月的广东已初显闷热,40岁的思政课教师甘相伟照例在课前手持着话筒带着学生喊:“我是最优秀的!我是独一无二的!”课上到一半,有学生在台下已是东倒西歪。

2023年底,甘相伟上思政课。澎湃新闻记者 葛明宁 图
甘相伟并不在乎这些出路也许是厨师、汽修工人的学生如何评价他。2021年底,他来这所职业技校任教,带着辛苦换来的傲人标签——曾经的北京大学保安,兼旁听生、励志偶像。在学校的接待厅刚一见面,他就给记者送上三本自己写的书,由薄脆的红色塑料袋包裹着——一本是2012年公开出版的《站着上北大》,另两本是在离开北大后自行印刷的《从北大起航》、《和北大齐飞》。
2008年,甘相伟带着找寻人生意义的慷慨志愿到北大,前后遇到的,正是中国经济和城镇化狂飙式发展。当时,舆论每天都在提倡个性,社会上常有一个靠着“金点子”发家致富的传说——惊人之语会被传诵,“不走寻常路”能得到大肆宣扬。保安旁听文史哲,考上北大成人教育的故事令人鼓舞。
在一些缝隙时间里,甘相伟到处演讲,讲自己11年在北大边当保安边听课的经历,一遍遍地告诉听众,要找到自己的优势、相信自己、找寻自己想要的生活。
离开北大是一条分水岭,随着“励志”潮退去,关注他的人也渐渐稀疏。2018年,甘相伟到武汉传媒学院当辅导员,一年之后难堪压力辞职了;赋闲两年后,他去上述职业技校教书。
甘相伟对记者描述,他从不甘于平庸人生,想闯出来成就自己。这个想法一直追赶着他,但他又无处可去。
以下是与甘相伟对话整理成的口述,部分内容摘自《站着上北大》:
喧嚣与沉寂
现在这份工作,是北大的校友帮我介绍的。我四十岁了,想要安定下来。我又喜欢温暖的地方,广东这里的气候好,房价也还可以。
疫情以后,我已经三年没有去演讲了。我以前到处去做讲座,不是很频繁,大概一个月两回,一次出场费三五千元。
过去,有记者来采访北大保安队,保安队长知道我好读书,就会推荐我。后来,有一些中学和大学来邀请我演讲,让我给青年人树立一个榜样,看看我在那么艰难的条件下,都能好好学习。
演讲的时候,我对台下的听众说:偏科学生不要害怕,可以分几步走。如果你考不上本科,可以先读个专科,然后再读本科、读研究生。有的人到了研究生才找到自己爱的专业,有的人本科读不了北大,博士才到北大,或者出国留学,国外绕了一圈,后来到北大当老师了。

下面坐着几千个学生,讲完了,还要给他们签名,鼓励他们追求梦想,我觉得蛮有意义的,蛮自豪的。
印象里,我被人怼得最严重的一次,是在北京中关村图书大厦演讲,有人提问:“你为什么不学数学呢?学数学对国家更有贡献。”
我只能说:“我喜欢文学,你喜欢数学,这不矛盾,没必要跟我抬杠。”
那时候每到周末,北大有一个旧书市,我们可以去挑选。我喜欢周国平、史铁生的散文,我一共有五千多本藏书。我还读了一个成人教育的学位。考北大的成人教育,考的科目是语文、英语和政治,如果要求考数学,对我会很难。
毕业之后,我还想留在北大,就在北大西门旁边租了一个房子,然后自由听课,又待了五年。我先去一所中学工作,但我觉得与北大自由的学习方式不一样,有点压抑,就不去了。又有一段时间,我想在业余时间不能太闲了,就去一个公司打工。都是暂时的,我下班以后都是在看书、学习、写作,想写一些人生感悟。
2018年,北大的校友给我找了一个工作,是武汉传媒学院的辅导员。当辅导员的压力太大了,要带十个班,340个学生,要24小时开机……我带完这一届就走了。
他们在看,证明给他们看
我从前的志向是往学界发展。我喜欢看书,记得读初中时,镇上书店卖的书少,当时地上掉一张纸,我都会捡起来看看。
当然,最初的时候,想的是要奋斗要走出农村。小学的时候,我经常考试第一名。村里人都觉得,我会有出息。有的父母会当着我的面批评自家的孩子,其他小孩对我甚至有一种“敌对”的情绪。
父亲去世的时候,我只有5岁,其他小孩总喜欢嘲讽我是“没爹的孩子”,我和他们对骂过,打过架,但不解决问题。我的三爹看我和姐姐太小,母亲一个人的确太艰难,硬是退掉了婚约,来到我家和我们组建了新的家庭。为了挣钱供我读书,他农闲时到城里去当建筑工人,听乡亲们说,连个小风扇都舍不得买。
我的爷爷多次对我说:“娃呀,以后长大,有出息了,万万不能忘记你的三爹啊!”
当时,孩子不上高中能免除一大笔费用,省下的钱主要用来盖房子——我以前也问过家里人对我的希望,他们说,只要你不在农村种地就好。在村里,因为我读书,才稍微家庭条件差一点。
父母希望我有出息是个好事,但另一方面,给我很大压力,太功利化了。

考上高中是我人生第二次去县城(注:指湖北随州广水市)。我小时候去过一次,先坐车到镇里,再转车到县城,那次是代表小学去参加数学竞赛,得了第二名。那时候,我以为我将来一直是第一名,但我到了广水一中,受了一点打击,一下子看到别人比你厉害。数学我真是花了很大的气力,成绩还是不上来。我还去找我们班数学最好的同学,让他们给我讲题。数学的思路我能理解,但是真到做题的时候,就不会了。
农村人没有什么出路,要么当兵,要么考大学,但是当兵这条路,我身体不好。当年,村里年轻人大多已经出去到广东打工。我会感到羡慕,他们回来跟我讲一些见过的世面,带了新的东西回来,比如饮料,以前农村哪儿有饮料,还有菠萝罐头,村里人从来没有吃过菠萝。
但我没有做生意的头脑,而且每天进货赚钱,再进货赚钱,我觉得“含金量”不够。
我高中时决定辍学去上海打工,想测试一下出去闯荡赚钱的能力,那时候,表哥他们已经出去打工,一个月能赚七百元钱,比一中老师工资低一些,但比一些乡镇干部工资高。班主任知道了,说,“你没有毕业证、没有技能,什么都没有。”我一意孤行,觉得自己能吃苦,但发现体力活真的干不了,搬不动钢筋。
几个月之后,我又打电话给班主任,说要回去读书。
去打工之前,我老想着,要考一个名校,(成绩)起码在湖北省排到前500名;但我在广水市都排不进前100名,根本没戏。
打工受挫,回来后心态已经不一样。我想,先读个专科,如果有机会再“专升本”。我能接受我上不了名牌大学这个现实。
“绕进去,绕出来,给谁看?”
高考成绩比我想象得要差,只能读个专科,在武汉读。但去省城读书,我还是蛮自豪的。我的高中同学有的在武汉大学读书,所以我能拿到课程表,我就开始到各个名校旁听,特别积极。以前,高中老师经常说,要走出广水;他们说,高中是小池塘,大学是大江大海。我想,在小池塘里能看到什么书,能见到什么样的老师?我在中小学阶段,没有听到一些有大智慧的人的话语,大学肯定不一样,大学教授讲课肯定涉及很多人生的话题。
我印象最深的是杨叔子的讲座,他是一个机械工程专家,但会讲《道德经》,要求自己的博士生背《道德经》,里面的哲学话语很有意思,“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无中生有”,天地宇宙,是大本大源的问题。

20岁出头,我一直闷在自己的世界里看书、学习。那些大人物,都是把儒释道打通的人,读古书的人都是很厉害的。我觉得,年轻时积累很重要,将来舞台多大,何必急一时去赚钱?
大专毕业以后,我先到广东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了一年,觉得满足不了我的精神需求,就到北京旅游。有一个老乡说,可以介绍我在北大当保安,我就去了,一个月六百块钱,住八个人一间的宿舍,不包吃,不过可以吃北大食堂,很便宜。

身着北大保安制服的甘相伟。图片来自互联网
北大保安三班倒,一个班八小时,站岗大概两三个小时,其它时间要巡逻、搞安全检查,保证学生的自行车不要被偷。那是很辛苦的,烈日炎炎、寒冬下雪,我都要在那儿站岗。
我见过北大夜晚的宁静,看过早晨第一束阳光出来,北大看朝阳最好的地方是在未名湖。很多人到北大来,在那里合影,但我们天天绕着湖走。
最好的是上早班。这样就可以晚上去听讲座,(晚上)七点到九点都是讲座。我没事就很早去,坐前三排。
保安队里,也有其他人喜欢学习。有一些高中毕业生,可能是家庭条件不好,没有上大学,他们当保安,也想业余看看书,听听课。
我后来考上了北大的成人教育,每半年大概开三四门课,把它修完就可以了,有一些是北大的教授来上,还有一些是博士生来上。

在《站着上北大》前后,甘相伟一度得到很多的关注与追捧。图片来自互联网
有一些课程要写论文,我不喜欢写论文,我觉得论文干巴巴的,没有情感的流露。像一些书的来历,版本不同,我又不是专门的学者,这不是我要研究的。
“三大批判”(指康德的哲学三大批判)我也不会去读,买都不会买,我觉得我哲学脑袋不够,这些书绕进去,绕出来,给谁看?
在北大听课,我从来不找老师合影,有的人专门找著名教授合影,我觉得没必要。不过,曹文轩请过我们这届学生吃饭,那门课人比较少,学期结束了,他感谢我们的支持。
有一次科学哲学学者吴国盛开讲座,我问他:“是不是科学技术爬到山顶的时候,佛法已经在那里等着了?”我忘记他怎么回答的。
陷于未完成的使命
我一直想写一些东西,高中的时候就在想,人生怎么才能有所成就?就想著书立说。看到圣人说的话,穿越千年而不倒,我十分羡慕。我想,每个人有不同的特色,我有我自己的经历和感悟。
要问我独特的经历是什么?还是我大专毕业之后敢去当保安,敢走不一样的路。
古人讲“文章经国之大业”,他们把文章看得多么重要,古人只要文章写得好就能做官,凭着自己的个性、风格。那时候的心灵比较自由。
到现在为止,我还每天在网上听课,每天学习。

甘相伟任教学校的墙壁上,仍有标语鼓励着学生自信、当更强的自己。澎湃新闻记者 葛明宁 图
我小时候认为自己将来要出去闯荡、有所成就的想法是因为“死亡教育”,父亲去世的场景,我现在还会回想起来。母亲脾气不好,父亲去世对她可能是个刺激。每到我爸的祭日,我爷爷奶奶都会面对山坡,朝他坟的方向哭——我当时想,既然人都要死,百年以后我们都不在了,活着的意义是什么?
我老在想,如果没有留下一点痕迹,对不起人生几十年。
我对文字比较敏感,老师一教我就马上会背,语文里面有很多古典诗词,诗人会在里面谈到自己的人生意义。我还记得,少年毛泽东所写:“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但是,我还是困惑,想去解决它。上高中时,有一些不能触动我的心灵世界的课,我听不进去。那些老师没有心理学背景,也没有在外面的世界闯荡过,回答不了我的问题。另外,更主要的问题还是,这是我的家事(指父亲去世)。我不想把这种很痛苦的事情讲出来。我不敢。我不好意思。
我旁听的时候,一直在困惑这种“生老病死”的问题,直到四十岁以后,我才有些放下。我读了南怀瑾的书,他说,要放下,连“放下”本身也要“放下”。
这些年,不工作的时候,我逛书店、买书,要不就去旅游,几乎哪里都去过。过年的时候,大年三十我都不回去,过几天再回去,走亲戚访朋友。
母亲在随州和我姐住。母亲一直知道我喜欢读书,现在我也不问她要钱,不用她操心。我那些表哥、表弟,以前考试都考不及格,但学一个焊接的技能,亲戚朋友凑十万块钱,慢慢地开个店。做生意的,到随州买一套房子很正常。我早年也羡慕过他们做生意,现在读了书,逐渐不羡慕了,我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没有过去那么纠结。
去年,爷爷去世了,我才回去一次村里,平时很少回去。村里已经没什么年轻人了。老人们都知道我读书,在北大当过保安。他们看到了我,也没有什么话可说,只说:“哎呀,你怎么还没结婚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