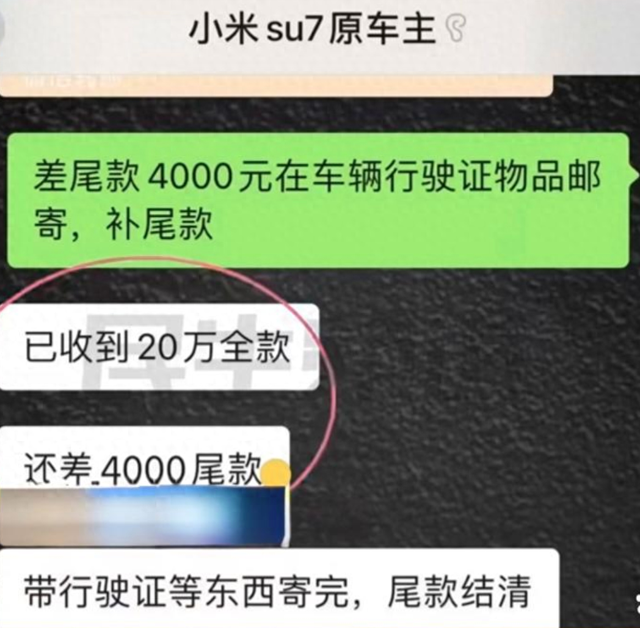“年前收到起诉书了,但还没有接到开庭通知,我也在等。”3月22日下午,大皖新闻记者联系上张某侨(化名)的生父张先生,他正在地里干农活。时隔多月,张先生提及此事,语气仍很沉重,"我一个农民,啥都不懂,只知道杀人要偿命。"2023年5月,山西运城10岁男童张某侨失联20天后被确认身亡,而犯罪嫌疑人竟是生母与继父。

图为遇害男孩生前的照片。
张某侨失联后被确认死亡一事,曾引发巨大的关注。临猗县公安局当时通报称,2023年5月23日找到失踪人员张某侨,已确认死亡。目前,犯罪嫌疑人谢某某、王某某已被临猗县公安局抓获,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2023年7月20日,临猗县公安局将案件移送到临猗县人民检察院。10月12日,又被移送至运城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之前移送至临猗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因为案件涉嫌故意杀人罪,可能判处无期以上刑期,所以检察院改变管辖,又将案件移送运城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张先生曾对媒体表示。
“去年11月我已经拿到了起诉书,但是现在还没有通知开庭,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3月22日下午,大皖新闻记者联系上张先生,其告诉记者,自己接受了法律援助律师,也提了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现在也在等着开庭通知,但对于起诉书指控的罪名,张先生并未透露。
自从小儿子的事发生后,张先生情绪一直不太好,“没什么心情,心里难受,现在主要在家种地,其它的想等孩子的事处理结束后再说吧。”
在与张先生的谈话中,记者也获悉,事发后,两名嫌疑人的家属暂未联系其前来道歉或要求出具谅解书。
对于未来的审判,张先生表示,“自己是个农民,啥都不懂,只知道杀人要偿命。”在案发后,张先生也多次公开表示过自己的态度,要求重判两人。
此前,大皖新闻曾多次追踪报道此案。2023年5月4日,临晋镇居民谢某某向临猗县公安局报案,称其10周岁的儿子张某侨5月3日凌晨在临晋镇下豆氏村离家出走未归,请求临猗县公安局帮助寻找。
同年5月8日,临猗县公安局发布协查通报称,有线索请与临猗县公安局刑侦大队联系,公安机关经核实后给予1万元奖励。
同年5月23日,“失联”约20天的张某侨被确认死亡,遗体系在继父王某某老家下豆氏村的墓地被发现。警方抓获的嫌疑人,是张某侨的生母谢某某和继父王某某。
此前报道
山西10岁男童遇害 继父曾冲镜头痛哭喊话"要找到娃"
10岁的男孩靠墙站在空调外机上,对着屋内人哭喊“别打我”。同一时间,一根伸出窗外的长棍被挥舞着不停逼近孩子,连续拍打,男孩随即从5楼跳下。男孩的坠楼视频引起关注,2023年6月26日晚,合肥长丰县公安局发布通报称,坠楼男孩全身多处骨折,肺部挫伤,相关情况正在调查。
将时间指针拨回一个月前,山西运城,另一名10岁男孩的死讯也让众人感到震惊和愤怒。
五一假期过后,运城临猗县本地人的朋友圈、抖音都在接力转发“离家出走”男孩侨侨的寻人启事。5月23日,男孩遗体在其继父村庄周边的墓地被发现,男孩的母亲与继父作为嫌疑人被捕。
案发后,这个晋南县城中流传起不少关于侨侨继父王某虎的家暴过往,曾经的邻居们也在努力拼凑短暂相处中那些“可疑”细节。
2020年5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国家监察委员会、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明确了履行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义务的主体和情形。2020年10月,强制报告制度被列入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成为法定责任。
到今天,《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发布实施已过3年,但在执行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难题。2020年5月至2022年3月,检察机关办理相关案件中涉案线索来源于强制报告的共2854件,发现应当报告而不报告案件1604件,推动追责299人。

孩子本该在一个安全、有爱的环境中成长,10岁男孩侨侨殒命前,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如何发现并保护一个正在被伤害的孩子?

侨侨最后就读的里寺学校。王倩 摄
独居的孩子
罗晓燕也疑惑过,为什么四年级的孩子一个人住。
今年4月,侨侨的母亲谢某多向罗晓燕租下了两间临街门面房,一年租金9000元。签合同的闲聊中罗晓燕得知,谢某多准备在这里开一个美容店。过了几天,罗晓燕看到一块红底黄字的“舞娘美颜”招牌挂了起来。
谢某多告诉罗晓燕,比起做生意,租住在此是为了方便孩子上学,儿子只要过条马路就能到对面的里寺学校。
入住后,罗晓燕却发现,隔壁的孩子总是一个人住,到了周五母亲才会出现。罗晓燕这才记起,自己早就见过这个总是独来独往的男孩。罗晓燕问过谢某多为什么放心孩子一个人,得到“十几岁了,锻炼一下自理能力”的回复,便不再多说什么。
拉起卷闸门,走进房间,很难看出一个10岁孩子的生活痕迹。出租屋里没有玩具、没有书本,只有一张不到一米宽的折叠钢丝床,再往里走是没有窗户的套间,右侧并排放着两张美容床,另一边则堆着用塑料袋套起来的药品、厨具和日用品,角落还有生父张岳买给侨侨的自行车。

谢某多租下的门面房就在侨侨学校的对面。王倩 摄
这个春天起,赵宏发也发现,孙子赵卓的同学侨侨开始频繁出现在家里。
儿子和儿媳在南方打工,赵宏发和妻子留在临猗本地一边料理农活,一边照顾两个孙子。许多个傍晚,侨侨跟着赵卓一起回家。他会安静地坐在小凳子上等着赵卓吃完加餐饭。赵宏发邀请侨侨一同吃些,他都礼貌地摇摇头。“应该还是想吃的,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呢。”赵宏发的妻子也会问起侨侨,一个人住怎么吃饭,他回答说,“我妈说了,一天三顿在学校吃饱,回到家没饭。”
有一回星期天,侨侨并没有被母亲接回村,他来赵卓家看电视,到了饭点便“知趣”地离开了。赵宏发问他回去怎么吃饭,侨侨回答说“吃馍馍”“有酱呢”。
赵宏发的妻子记得,侨侨只在自家吃过一个鸡腿。 她去熟人家里吃满月酒,席面上一盘鸡腿没人动,她打包回来,晚饭的时候热了一下,那回侨侨没再客气推脱。
等到赵卓吃完饭,两个人就跑出去玩,再叫上住在同村的同学小宇。有时他们在房前的巷子里嬉闹,有时候会跑上村外的大路,村委会放露天电影时孩子们也会聚在那里。等到天色渐暗,同伴们各回各家,侨侨则回到那个空荡的屋子。
四年级第二学期以来,因为做同桌,小宇几乎是班里和侨侨最亲近的同学。小宇怕黑,他佩服侨侨敢一个人住,“我问他关灯了害不害怕,他说他有手电”。
即便家离学校只有几百米,放学时,赵宏发也要去接孙子,有时候他在地里侍弄果树误了时间,会接到班主任的电话询问。“你给他接回来,他再出去玩,心里就踏实了。”小宇母亲张雪娇告诉记者,家人每天都要接送小宇上下学。赵宏发和张雪娇猜测,侨侨不用接送,可能是家长和老师打过招呼。
“那个孩子看着有些孤独。”赵宏发说。有时,早晨6点多,他出来给孙子买早饭,会看到背着书包的侨侨提前1小时就坐在校门口的斜坡上等着上学。

谢某多告诉过房东罗晓燕自己的计划,五一假期过后她要对出租房进行装修,好让美容店早日营业。“但她说店开张了也不会住在这, 孩子还是一个人住。”罗晓燕说。

侨侨送给同桌小宇的“水果刀”。 王倩 摄
“强制报告”规定的9种未成年人遭受不法侵害的情形中包括“未成年人被遗弃或长期处于无人照料状态”。与法律规定强制报告的几类主体不同,邻里有权利报告而非义务。面对这个外来的孩子,他们抱有同情,也保持沉默。
赵宏发和妻子问起过侨侨父母的职业,“妈妈是走事的,爸爸是开车的。”问一句,答一句,男孩没有吐露更多。“他也没有说过他们是离异家庭,我们都以为是亲生父母,只是觉得把孩子一个人放着,家长有些不负责任。”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宋英辉,是我国少年司法领域最资深的专家之一,他参与了最新《未成年人保护法》的修订工作。“让未满16岁的孩子独立生活,这是法律规定不允许的。这种无人照顾的情况也可以报告,问题是有关的主体是不是发现了?”宋英辉告诉上观新闻记者。
“拉黑”的离异夫妻
5月4日清早,罗晓燕看到谢某多坐在门前的台阶上,望着街对面的学校,眼睛红红的,像是刚哭过。罗晓燕上前询问,谢某多告诉她,孩子丢了,想看看孩子的生父会不会把侨侨送来学校。
“我问她怎么丢的,她说是孩子偷钱,打了几下。还说平时打几下就回来了。”罗晓燕给谢某多支招,让她抓紧去调监控。
罗晓燕疑惑为什么不能给孩子的父亲打电话,谢某多告诉她,两人离婚了,对方不接自己的电话。罗晓燕这才知道,原来新租客一家三口是重组家庭。
这天上午10点多,侨侨的生父张岳接到了村长电话,得知小儿子不见了。此时距离自己上次见到孩子已经过去10个月。
2021年11月,张岳和谢某多离婚,大儿子跟着张岳生活,二儿子跟着母亲谢某多。
像许多农村离异夫妻一样,两人再无来往。离婚后,谢某多也再没有来看过大儿子。根据张岳讲述,自己不知道谢某多何时再婚,也不认识她的现任丈夫王某虎,对小儿子近一年来的生活并不了解。
2022年6月底,父子俩最后一次见面时,侨侨告诉张岳,母亲已为自己办理转学。张岳说,此后自己去县城的几所学校找过,都没有找到人。“孩子原本有手机,但是那个号码停机了,就联系不上了。”
张岳告诉上观新闻记者,侨侨转学到县城后,因为想探望孩子,自己给谢某多打过几次电话,两人爆发了争吵,随后自己被谢某多“拉黑”,“人家说既然分开了, 她已经成家,就不要再影响她的生活。意思是再去看孩子就是打扰她的生活。”“虽然看孩子是我的权利,但也要经过人家同意。”
“他也没什么爱好吧。”当记者问起侨侨的兴趣爱好时,张岳显得有些茫然。转学前,小儿子在临晋镇西关小学读书,张岳说自己曾经多次去学校探望,但见面多数是在学校熄灯前的洗漱时间,他没有发觉侨侨的神情有何异样,“给孩子送点吃的,每次就见十几分钟,晚上黑咕隆咚的,也看不清。”
时隔几个月,小宇妈妈张雪娇依然能记起别人提到父母离婚时侨侨的反应。有一回张雪娇遇见两个孩子一起玩,她随口问起侨侨一个人住在出租房的事,儿子小宇在旁边插话,“他爸妈离婚了”。“看着侨侨脸色马上就变了,特别阴沉,我都被吓到了。”张雪娇连忙解释,”侨侨你别生气,小宇是无心的。”


里寺村内部。王倩 摄
侨侨最后出现的影像在临晋镇下豆氏村村口,监控记录下他下出租车后往家里走的画面。张岳查了下豆氏村临近几个村庄的监控视频,再无孩子的踪影。
侨侨失踪后,张岳曾经得到一条线索。他组织了20多个人去寻找。张岳打电话给谢某多想要通知这个消息,“给她打电话,她就在那里大吵大闹,说我以前也不管孩子,现在怎么怎么样。”
罗晓燕记得,在临猗警方发出协查通报前后,谢某多和王某虎回过一次里寺村的出租房。两人坐在门口的台阶上,向邻居们哭诉孩子还没找到。“那个男的(王某虎)说,孩子不听话,老是偷东西,这次又偷拿了七八百块钱。”一名男邻居建议两人去运城的网吧找找看,同时这位邻居又觉得可疑,“既然发现孩子拿了钱,为什么没有收走,小孩反而拿着钱跑了?”
随着时间推移,县城里流言四起。5月10日,有十几万粉丝的本地博主@ 国舅爷 分别帮张岳和谢某多拍摄了寻子视频。见面时,戴着口罩的谢某多不怎么说话,一直在哭。侨侨的继父王某虎情绪激动,一边痛哭,一边冲着镜头喊话,“我是后爸,我澄清不了,我现在只有安安静静把娃找出来,才是对我最大的澄清。”
5月24日,一则警情通告,让持续发酵了大半个月的儿童失踪案终于有了定论,临猗县公安局于23日找到失踪人员侨侨,已确认死亡。犯罪嫌疑人谢某多、王某虎已被临猗县公安局抓获,案件在进一步侦办中。
隐蔽的暴力
在“强制报告”写入《未成年人保护法》之前,2018年起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检察院率先建立了“强制报告”制度。2018年至2020年三年间,萧山区检察院共接到未成年人遭受不法侵害的线索38条,成案14件,其中性侵案件11件,其余2件是“虐待”,1件是“故意伤害”。华东另一城市人民检察院也在调研中发现,非性侵类案件的报告率较低。与性侵相比,暴力是更加隐蔽的侵害。
看到临猗县警方的通报后,曾经与这个重组家庭有过短暂相处的邻居们,开始努力拼凑那些不同寻常的细节,才发现也许孩子早已置身险境。
4月28日,五一假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里寺学校放学后,罗晓燕听到一墙之隔的出租房传来很大的响声。
“声音很大, 喊一句,啪的一声,再喊一句,再啪的一声。” 罗晓燕听到训斥的声音来自男性。最初还有孩子的哭声,但马上被呵斥止住,剩下的只有分不清是用手还是用皮带抽打的声音。
罗晓燕也想过是否应该去制止,但又转念一想,“父母教育孩子是家事”,自己还是不要过问,更谈不上报警。罗晓燕反复几次提到,“谁知道,他不是亲爸啊。”
四年级上学期,侨侨住在离学校一公里多的奥运花园小区。老住户胡汉民记得,去年夏天最热的那段时间,每天早晨自己打完太极拳休息时,就能看到侨侨围着小区花园开始跑步。“孩子跑得特别快,有时候还会看一下手机,应该是给限制了时间。”胡汉民见过,有时候一个男人骑着电动车跟在后面,小孩边跑边哭。那时邻居们都以为,接受严格训练的男孩今后要走体育生的路子。

侨侨一家曾在临猗县城另一小区租住。 王倩 摄
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下豆氏村一位在侨侨继父王某虎家附近的邻居介绍,王某虎脾气暴躁,有家暴倾向。这位邻居曾听王某虎的前妻抱怨,“王某虎打人不光用手,看见什么工具就用什么打”。
侨侨对同桌小宇吐露过自己的秘密。“他说亲爸对他可好了,后爸对他不好,他犯一点错,后爸就用皮带抽他。”小宇回忆。有一次课间,侨侨撩起上衣,小宇看到了他的伤疤,“他肚子上有一个可大的伤口,全班同学都知道。”
这学期侨侨曾经左臂骨折,打着固定来学校上课。“我问他胳膊怎么弄的,他说是从楼梯摔的,可我觉得不可能。”小宇说。搬到“舞娘美颜”之前,侨侨还在里寺村的另一处民房二楼短暂居住,小宇去过那里,“那个公寓的楼梯一节一节的,不可能摔成这样,除非是被他后爸打的。”
赵宏发见过侨侨左手手指骨折缠着纱布。问起缘由,孩子回答同样是从楼梯上摔下来。赵宏发没有过多怀疑,也没有继续追问,“他说手指头还要做手术呢。”在赵宏发妻子的印象中,骨折的同段时间,侨侨的脸上有伤痕,戴着口罩也能看到鼻梁上的淤青。
宋英辉告诉本报记者,立法时,他曾经建议“就近就急”的原则,“你离他很近,发现危险,或者是很紧急正在实施侵害,一般公民也应该报告,但后来觉得操作起来比较困难,法律没有规定。”
《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规定,学校、医院、儿童福利机构、宾馆等机构的工作人员,发现未成年人受到侵害,必须向公安机关报案,如果相关人员、单位发现未成年人遭遇侵害的线索却不报告,将要承担法律责任 。
本报记者曾前往侨侨最后就读的里寺学校,校长樊向平婉拒了采访。老师和医生在工作中是否发现了侨侨遭受或者疑似遭受不法侵害,尚需要相关部门的调查结果。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强制报告执行过程中,仍然存在着部分强制报告主体职业敏感性不强,履行报告义务情况不符合预期等问题。
浙江杭州检察院检察官曾在2019年对杭州市部分小学老师调研发现,八成的老师认为报告上级主管部门、报警会扩大事态的严重性,不利于儿童成长。
蔡志洪是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检察院的一名未检检察官。去年12月,在一起组织卖淫案中,她发现多名被性侵害的未成年女孩,曾因严重的妇科疾病在多家医疗机构就诊。接诊医生在发现这些未成年人受到严重侵害,且没有法定代理人陪同就诊后,并没有及时报警,最终8名医师受到处罚。当问到这些医生为什么不报警,他们回答蔡志洪,“不知道需要报警。”
为进一步推动强制报告制度落实,引导负有强制报告义务的单位和人员依法履行报告义务,2022年5月7日,最高检编发了6起因不履行强制报告义务被追责的典型案例。

距离里寺村不远处,不少楼盘正在加紧建设。 王倩 摄
里寺村位于临猗县城城郊,走上几百米就能到县城主街。和罗晓燕一样,不少村民将房子隔成单间或者套房对外出租。赵宏发家的二层小楼也有几间房子出租给了在不远处建筑工地务工的人。赵宏发说,来往租户并不需要在村委会进行登记。
“假如村委会、居委会发现了儿童受到侵害不报告,肯定有责任。如果因为人员流动性大,管理上有漏洞而没有发现,可能很难追责。” 宋英辉建议应在人员流动性较大区域对儿童情况进行动态监测。
记者走访了侨侨在里寺村的两处住处。在第一间公寓,一名已经在此租住一年多的住户告诉记者,侨侨出走失联的消息在抖音上连续刷屏的那几天,他也多次见到过寻人启事,“ 这么大的事咋可能不知道。”但他并不曾留意,这个男孩和自己在同一个院内住过。
因为受不了来往路人的议论,案发十多天后,罗晓燕花了50元请人将隔壁的招牌摘了下来。在临猗县城,关于这起案件的讨论热度已经逐渐褪去,但回想起那个“礼貌”“懂事”的男孩,小宇的妈妈张雪娇还在反思,“还是保护得太少。要是知道这种情况,我当时就应该多关心他。”
(文中侨侨、罗晓燕、赵宏发、赵卓、张雪娇、小宇、张岳均为化名)